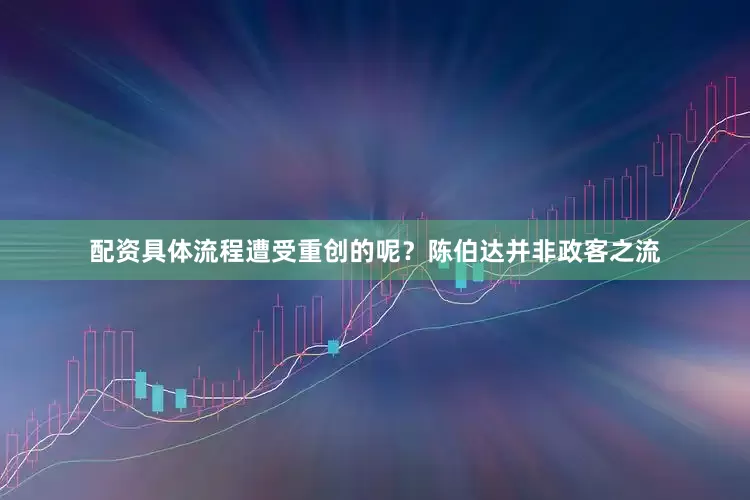
曾彦修追忆陈伯达:他并无意投身政坛(曾彦修)

陈伯达先生,堪称一位既聪慧又多才之人。在我眼中,他的才华似乎超越了学识,而学识又胜过品德。然而,遗憾的是,他的品德似乎因职位而遭受了损害。
威信骤降。
陈伯达凭借其文采一度名扬四海,曾一度成为共产党内的第四要员。然而,他又是如何从云端跌落,遭受重创的呢?
陈伯达并非政客之流,他素无涉足政坛之志。政客需频繁奔波,四处联络,发表演说,而此等技艺,他实不擅长。即便是在正式场合发言,他亦难以坚持五分钟。在延安时期,我察觉他更倾向于成为一名政论家。他渴望自己的文章能够引起全党的关注,乃至全国的瞩目,那时他便心满意足。他平生的著述,无不围绕最高领导层的意志,均系奉命而作。直至1966年“文革”期间,他加入《人民日报》后,仍能即时挥毫泼墨,创作出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等时评佳作。
《狂飙扫荡牛鬼蛇神》,作为“文革”初期的一纸彻底颠覆常规的紧急号召,此口号犹如一颗震撼全国的核弹,谁能不感到震惊?历史事实表明,此文一出,陈伯达的历史角色实则走到了尽头。他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达到了极致,因为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口号提出后,便再无其他可被扫荡的对象。
所以,不是1971年庐山会议批评他后,他才不重要了,而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他实际上就不重要了。不仅如此,这篇文章发表以后,他的活动,反而变成了他的罪行的材料,说他是在为林彪服务,破坏了毛主席的威信,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头上。“文革”的事,是江青在那里指挥,陈伯达也根本不大会做这些事,只有江青一人敢对陈左一声老夫子,右一声老夫子。其实是挖苦他,轻视他,说他除写几篇文章外,无用了。
从此,陈伯达就被打倒、被批判了,成了林彪集团头目之一,又成了反革命。
“呵,呵,瞧这厮又来了。”随后,其他几位亦纷纷跟风讽刺。当时,我深感陈伯达的威望一落千丈,这不只是个别对他的态度,而是宣传部的众多处长都将他当作笑柄。
除了于光远之外,在延安时期,众人对他无不怀有敬意,然而到了1951年,却纷纷对他冷嘲热讽。我不认为这种转变会毫无缘由。如今,于光远尚存于世,而那些昔日的同仁,却已长眠于尘土之中。
我与陈伯达关系。
我与陈伯达的交往并不频繁,仅有几分直接的个人联系。回溯至1941年夏日,正值整风运动前夕,彼时他似乎并无明确的职务,仅以一位重量级的文化名人身份居于延安。传闻他曾担任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,但若此言非虚,那也不过是虚衔而已,他本人对此类事务鲜少过问。在其一生中,无论身处何单位担任何职,他总是以一个轻松放任的“甩手掌柜”形象出现。
在1939年至1940年间,延安地区成立了众多研究机构,这些均由上级部门发起,包括资本论研究会、哲学研究会、马列主义研究会等。我受马列学院的委派,参与了其中的两个研究会,一个是陈伯达负责的三民主义研究会,另一个则是王明负责的马列主义研究会。在陈伯达主持的三民主义研究会中,我聆听了他的多次讲座,尽管我们对于其中的内容所知有限,但仍然认真聆听他的讲解。
在延安时期,自1941年夏日始,他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一职,而我便是其下的一名研究人员,隶属经济组。陈伯达先生对我们产生的深远影响,便是他所倡导的“个人讲学”。每当夜幕降临,晚饭过后,我们便会带着板凳前往他的窑洞,聆听他悠然自得的谈天说地。
陈伯达居于简朴的窑洞之中,屋内设有一小炕,他正卧于炕上。我们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,与他相差十数年,他堪称前辈,体型微胖且不高大,性格随和。窑洞空间虽仅能容纳十余人,我们无法入内,便在外聆听他的闲谈。陈伯达无所不谈,天南地北,信口开河。他偶尔还会提及与毛泽东的私密对话。在延安,毛泽东的窑洞中,除了处理公务之外,能随意闲聊的人似乎唯有陈伯达一人。周恩来、朱德等皆是讨论公事,而陈伯达前往则是聆听毛泽东的闲聊。毛泽东亦需放松,寻求闲聊的对象。陈伯达阅读广泛,思想活跃,有时会邀请他参与。他曾向我们传授,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的家书值得一读。过去,共产党对曾国藩极尽贬低之能事,为何还要读他的书呢?陈伯达亦认同,曾国藩的家书文采斐然,内容实用,阅读并无害处。许多马列主义者,包括我们这些青年,以及那些入党二十余年的中年人,普遍对中国文化持批判态度,对曾国藩的批判尤为激烈。陈伯达曾提到,毛泽东提出“自然而然革命化”的观点。他认为,毛主席的这一观点甚佳,因为强迫革命不可取,有些事情需要等待,让它自然走向革命化会更容易实现。
总体来看,陈伯达在延安时期的政治影响力尚属有限,彼时他尚非中央委员,然而,其威望却超越了延安所有文化人士,甚至远超周扬等人。据推测,当时延安的党内和党外文化人士总数可能高达数百人。
陈伯达在延安整风中的重要性突出。
延安整风运动可追溯至1941年毛主席发表的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一文。大约在1942年左右,陈伯达撰写了两篇具有深远意义的文章。这两篇作品对于奠定毛泽东同志崇高威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,它们对党史的研究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新解读。然而,如今我们不再提及它们,因为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。实际上,在延安时期,我们曾多次研读这两篇文章。一篇名为《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,另一篇则题为《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》(该书在解放后出版单行本时,或许更名为《关于十年内战》)。
这两篇文章在理论层面首次明确指出,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始终正确无误,他是无可争议的唯一正确领袖。这两篇文章对于确立这一观点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因此,在延安整风期间,陈伯达在支持毛泽东、强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且至高无上的领袖方面,贡献了巨大力量。当时,这两篇文章深受大家拥护,实际上对我们这些年轻一代坚定地支持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“蒋介石杀人流的血,真是太多了,真是太多了,真是太多了。”连用三次“真是太多了”,令人痛心疾首。即使时至今日,提及此事,仍不禁泪流满面,所谓“言有尽而悲无穷”。陈伯达的这篇文章,自共产党成立以来,实属难得的感人佳作。无论是用于《评中国之命运》,还是用于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,其笔尖都饱含感情,字里行间充满了对“杀,杀,杀”的强烈控诉。
陈伯达的教训
陈伯达亦对毛笔字情有独钟,其书法造诣堪称天才。尽管练字之数不多,然而其笔触之精湛,既豪迈又不失潇洒。他所出版的几本小册子,封面上的书法均出自其手。在那个时代,我们无不对他心生敬佩。
陈伯达其人,留给后人的教训尤为深刻。他才华横溢,却未投身学术研究,其全部精力投入于迎合当时的政治需求。无论是对个人仕途的追求,还是对政治需要的迎合,他皆以文章和书籍为工具,篡改历史事实以佐证己见,而非以事实为基础构建自己的历史观点。因此,陈伯达一生笔耕不辍,然今日审视其作品,在学术领域具有坚实根据、经得起推敲的,恐怕寥寥无几。
陈伯达的一生,犹如一面映照世态人情的明镜,对于热衷于理论史学的众人而言,堪称宝贵的借鉴。他之所以成为如此人物,缘于其聪明才智,却缺乏扎实深厚的真才实学。倘若他能够效仿党内其他学者,如范文澜一般,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,其成就或许能超越范文澜等前辈(范文澜虽具真才实学,却最终被简化的“阶级斗争论”所束缚)。陈伯达的一生,实则与苏联的米丁、尤金、维辛斯基、李森科等所谓学者相仿(然而,我认为陈伯达在智慧上远胜于他们,那些人不过是几柄利刃而已),他们的学说随时间流逝而失去价值,甚至沦为荒谬之谈。在学术领域,陈伯达并未真正有所建树。即便今日陈伯达是否被判刑,他的著作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,但影响有限。以陈伯达为鉴,我们得以洞察其得失。
不过,在判刑的人当中,最令人叹息的还是陈伯达,他不是张春桥、姚文元这类东西,他是1927年“四一二”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后加入共产党的。这一点,他自己是引以为骄傲的,他常给我们讲,虽然话说得平淡。可惜,一个人如果不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重,只是为自己的名、自己的位,而不去坚持事实,写多少书都没有用。在当时就有人看穿你这个东西不行,以后更会成为废品。我作为晚辈也算观察了这一类人70多年,我现在觉得任何东西,凡是不合历史事实的,随便你怎么讲,有些当时就被人耻笑,有些最后要破产。我觉得,陈伯达留下的教训非常深刻。一个文化人,一个作家,光赶时髦没有用,最后还要考虑到对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符不符合史实,对不对得起中国人民。
实盘交易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




